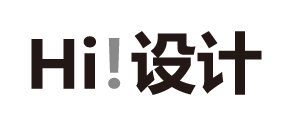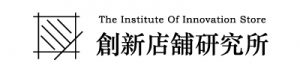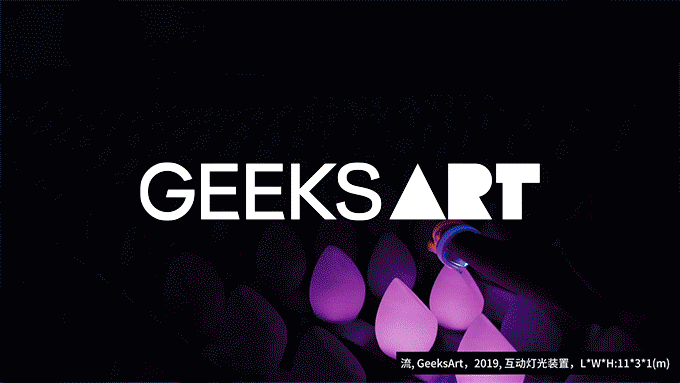2025年8月24日下午,由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主办的“半场”第三场展览《绝对初学者》在北京建筑大学开幕。本次展览由张早和谢舒婕策展,刷刷建筑和氙建筑联合参展。首先,策展人张早和两家事务所在展场进行了导览。然后,在开幕式上,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执行院长穆钧代表主办单位致辞,金秋野作为半场发起人进行致辞。随后,张早作为策展人致辞。接着,刷刷建筑的主持建筑师苏晓萌、氙建筑的主持建筑师王岩石和白河进行了分享。开幕式的最后环节是学术对谈,对谈由谢舒婕主持,华黎、晁艳、郭廖辉、黄伋、张早、苏晓萌、王岩石、白河参加对谈。
△执行院长穆钧致辞 ©韩一阁
△发起人金秋野致辞 ©尧迪
△策展人张早致辞 ©韩一阁
△刷刷建筑主持建筑师苏晓萌分享 ©尧迪
△氙建筑主持建筑师王岩石分享 ©尧迪
△氙建筑主持建筑师白河分享 ©尧迪
△对谈现场 ©尧迪
△对谈现场 ©尧迪
△对谈现场 ©尧迪
△对谈现场 ©韩一阁
整个展览空间被一条“问题的河流”贯穿。“问题的河流”从工作桌开始穿过一个“辩经台”,最终流向远方。“辩经台”的上方是芭蕉叶,这有着“园居生活,蕉下对弈”的隐喻。“辩经台”的地面被天然松针铺满,如松针铺地的古寺。芭蕉叶和松针随着时间变化,这给整个展览空间带来退化的时间性。这个“辩经台”引导人们席地而坐,讨论问题。这里也可以成为剧场的舞台。“河流”两侧的显示屏展示着两家事务所的项目介绍。
△开幕式现场 ©尧迪
△开幕式现场 ©韩一阁
△展览空间 ©朱雨蒙
△展览空间 ©朱雨蒙
△展览空间 ©朱雨蒙
△展览空间 ©朱雨蒙
△展览空间 ©朱雨蒙
△展览空间 ©朱雨蒙
本次展览展现了刷刷建筑和氙建筑在实践过程中的思考,也体现了他们不断发问,勇于探索的精神。
△策展人张早导览 ©尧迪
△刷刷建筑主持建筑师苏晓萌导览 ©尧迪
△氙建筑主持建筑师白河导览 ©尧迪
△开幕现场 ©朱雨蒙
△开幕现场 ©朱雨蒙
策展人
张早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谢舒婕 建筑师
参展事务所
刷刷建筑 atelier suasua
由苏晓萌创立于2019年,位于北京北新桥地区的草园胡同。工作范围包括中小型文化、商业、居住空间的建筑设计和改造更新。希望空间可以诱发身体、想象和环境之间潜在的交流,结合材料、手工艺与构造,使建筑物在建造完成后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生命体。
www.ateliersuasua.com
氙建筑 xian architects
xiān
山·气
第54号化学元素
xian氙建筑工作室
开展建筑设计与装置艺术创作
独具艺术性的探索
人与更广阔环境的深切关系
让人在日常之中
能觉察与自然宇宙紧紧相连
感受生命刻度的建筑艺术
对我们来说
建筑是对更广阔的存在
和生命潜力的提示
是对人所共通的内在
给于支持的具体行动
官网
展览信息——
展期:8月24日-9月23日
展览地点: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建筑馆一层展厅
策展人:张早、谢舒婕
参展事务所:刷刷建筑 atelier suasua、氙建筑 xian architects
策展团队:秦鸿昕、韩一阁、宫灵希
“半场”发起人:金秋野、李涵
主办单位: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我们在路(道)上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刷刷氙” “绝对初学者”的展览主题直接来自白河、岩石和晓萌三位均已涉足这个专业有20年左右的建筑师。说实话,我一度陷入了这个可能并不是那么令人费解的清晰题目,这会是态度端正的好好学习的作为么?作为名义上的策展人和一名经验丰富的建筑教育工作者,无论从职责上,还是从自我价值的角度,我都不得不尝试给出自己对题目的揣测。
直觉上,这种不留余地的命名后必须是百分百的执着,谦逊、自信,当然,也难免透露出些许,至少是以副作用的方式出现的,反学院意味。
并不是任意两家建筑事务所都能给出且同样认同这样的题目。我们回到展览的主角们:刷刷,suasua,风吹过树叶很爽朗的声音,一种纯粹自然的听觉经验;xian,氙气的氙,不易反应,迟钝而陌生,雾气缭绕的山。武断地看,两个事务所的作品产出如他们的名字一样稳定,刷刷更重存在和感知,而氙更重本质和精神。工作层面,他们都在积极地面对具体,真实与稳定地建立关联,让人不难确认,绝对初学者,并不是某种刻意的客套自谦。
他们明确地把这次展览等同于一次设计,希望把精神性,仪式感置入一个建筑学院尺度上令人“无所适从”的通属空间,在短时间内让它具体地成为一个自我领地。在这个空间里,除了展示自己的工作,更主要的,它将充满“绝对初学”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种“无所适从”形而上地理解为无家可归。它既是今日城市空间的类比,当这一属于学院的空间作为建筑师的展览空间呈现,用巴西利卡的布局,以绝对初学之名填补时,新动作不可避免地呈现为一种批评:它既是空间的,也是功能性的。
20个春秋的“绝对初学”,那意味着建筑学需要学的真的是很多,也在某种层面上说明着当代建筑学的困境。有这么多要学,恐怕是因为要成为具体的建造者,编织新意义同时,建筑师需要面对各种意义断裂,需要面对一座没有答案的现代废墟。因此,建筑师最好同时是考古工作者,史学家,意义修补者、重建者和泛技术层面的调停者。面对技术的井喷,建筑师无法投降,也无法自欺再建一个建筑的宗教。这么多问题,无目的的开放,共同体的弥散,不再有纪念碑的那种确切和封闭,它是不能完成的,因为不可完成,同时是仪式化的,认真求索的,也是不稳定的,未知的,震荡的,而后可以精良准确,也因而正确地去建造。
当我们以当代艺术的、库布里克的方式立起一根冰做的碑,或者是用棚屋的类型去塑造一个城市咖啡馆,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是学过了的呢?以一种自讽刺的方式在一个令人无所适从的现代空间里放下一座圣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关于问题的空间?
总之,在这座现代风暴造就的废墟里,我们得向前飞,但是必须向回望,你随着风暴飞得越快,身后的断裂风景就越多,当你想建立关联获得意义,却也正面对着无数猝不及防的碎片般的,而在于你,认为是急需回应、修补的当下现实,那么,建筑师,我们就无时不刻不在获得一种绝对初学的状态。
当然,这个判断越是明确,就越是自信且透露骄傲,那是大概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初学”。
意思是,我们在道上。
策展人:张早、谢舒婕
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