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中无人”的建筑师,到致力于城乡交互的设计师,娄永琪认为,从源头上思考,设计要起到更大作用,必须从个体的专业的创造,变成走向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创造。
B=《外滩画报》 L=娄永琪
B:“设计丰收”项目为什么选在崇明的仙桥村?
L:我们有个情结,想做点事情,觉得不能自己做,否则就只是自己的表达。开始是想,我们来搭个平台,让更多人一起做,一方面我们自己看世界,另一方面也看看别人怎么看世界。所以一定要找个有名的地方,大家愿意来的,用世界的知识来处理中国的问题。第一当然必须是农村,第二不能太远,否则我没时间去,第三要有关注度。三个条件一交集,基本就在崇明了。第四,我希望这个案例是能普及和推广的,因此不能找一个太方便的、已经被开发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弄好了,才有推广价值。我们也不希望光是外面的人去指导,他们本身也要有动力做一些改变。我 2007 年开始琢磨这个,当时崇明一个镇的副镇长很年轻,很想做一些事情,当地也有一些基础,比如是上海的商品粮基地,所以选了这个镇的仙桥村。
B:他们很支持这个项目,具体是怎么支持的?
L:我说不会从崇明带走一分钱,他们当然支持,不过主要是在道义上,允许你做。
B:三四年做下来,政府换届了吗?
L:换届了也还是支持的,其实也不需要多大支持,不反对就行。2008 年我们搞 workshop 的时候住在镇上的宾馆,第二天警察来了,把我们请出去了,因为宾馆没资格接待老外,只能住到县里去。现在我们都是住在农民家里。
B:农民最初对你们去做项目的态度是怎样的?
L:最早我们去村子,不能说像英雄吧,但差不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跑光了,没机会的人才留下来,他们对村子没什么信心。一开始看有大学教授、博士、硕士、老外整天往那里跑,他们觉得可能我们村子里有点什么,就有了一点信心,所以很好客。后面情况变化了。中国人的好客是这样的,很多时候都是表层的好客,面子文化,对彻底陌生的人是非常好客、慷慨的,走到深层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外人似乎更好。
我们一起做事情的不同团队,身份和目的都不同,有些学校的调研团队是纯粹做研究的,不会给村子带来利益,所以和他们的关系也不深入。我们做的是实际的事情,种地、做品牌、利用废弃的资源。比如改造了两个房子,一个叫“禾井”,一个叫“田埂”。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就像石子扔到水里,和村子产生了紧张关系,既改变了我们和村民的关系,利益重新安排后也会改变村民间的关系、村民和乡政府的关系,关系变化了自然也有冲突。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能是城乡互动里最有意思的。
B:你们和村子的冲突,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L:比如有段时间突然发现村支书不太支持我们了,我们也是后知后觉,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改变了村子的权力体系。其实说起来村子里也没多少权力,但是恰恰因为我们过去了,有新的生意,我们选择了这个农户做我们的供应商,他就赚钱了。而之前给不给你机会是由村支书说了算的,不是外人,可以想象这会和村支书产生冲突。
“禾井”也是一样,我们把那个房子改造成民宿,就要找人做服务。按村里人的观念,这个好处要归住得离房子最近的农户,不管我做得好不好,你一定要叫我。但是按城里人的观念,选择的标准应该是谁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结果我们选择了另外一家人,那个住得离“禾井”最近的人不来找我们,他和那一家吵架,说“你手伸得太长了”。
B:所以城乡交互,物理层面还是其次,关键是人与人的互动要搞好。
L:对,最有意思的是互动这一块,不是物理的东西,这些恰恰在表层以下。有人说,只有深圳的文化才能产生这样的城市/建筑双年展,其实这是非常国际化的东西,哪个城市或者企业肯出 3000 万,任何地方都可以办出这种水准的双年展。厂房中国哪里没有?双年展并没有长到土壤里去。怎么认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人,由此出发在土地上开发生意,才是“为城乡互动而设计”。
还有比如我们种田,老百姓对我们意见大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号称“自然农法”,一年只种一次,不撒农药和除草剂,草就长得比稻还高。农民觉得不好看了,本来干干净净的田,但这块地是我们租下来的,他们也不敢在我们田里撒除草剂,就在我们边上撒。
B:你们使用“自然农法”,应该也得保证收益吧?否则这个项目就不是可持续和可推广的了。
L:种田我们和老贾合作,我的态度是,我提一个问题,请不同的人和团队来讨论、解决,一起开发商业模式,生意上是伙伴关系。我不是真正的种田,我找老贾来种,老贾是保赚的,我是有风险的,我们给的钱比他稻子全卖掉还多。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现在的三农价值只开发了很小的一块,它的物的价值被开发了,背后非物的价值没有开发,比如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然而没有物,那些价值都是空的。看似种稻是赔本的,但是周边的生意如果开发出来的话,新的平衡就产生了。
现在来讲,乡村资源如此多,开发的人如此少,哪怕我是没有技术的创业者,也可以取得成功。这是基本的判断。剩下的就是怎么把体验、环境、知识变成商业模式。比如小孩都想认识各种作物,但是没有这种服务,乡村接下来要变得有吸引力,能和城市抗衡,要发展的是这一块,而不是粮食产量。我们想把没开发的三农价值通过设计体现出来,主要是模式的设计,怎么通过创意、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整合,增加价值或者创造新价值。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和建筑无关的事情。
B:你怎么判断一个项目是否成功?在你们已经在做的项目中,哪些算是成功的?
L:成功的标准,一是不靠政府扶持,是自下而上的,商业上是成功的;二是长期来看,这个经济如果放大 10 倍、100 倍,对社会是起正向作用的,这个我们称为“修复型经济”。如果这两点能实现,就是成功的案例。很多案例在商业上是成功的,但放大 100 倍,未必是好事。比如我们做的改造农民房,变成民宿,现在商业上还不成功,但理论上是会成功的,Happy Weekend(快乐周末)在商业上基本已经被证实是 OK 的。不过我们自己并不特别主张这种商业模式,为什么呢?对我们来说,这只是在意识层面特别有价值,让资源往乡村开始动,这是有价值的,但成为主要的商业模式就有问题了。因为像这种社区支持的旅游,如果你在当地待了超过 3 天,你的“碳足迹”是负增长的,但如果少于 3 天,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农民赚了钱是肯定的,却并不是可持续的,并不能放大 100 倍。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何让人在那里待超过一个星期甚至更长。这样你就必须带着工作去。目前我们想的是,中小型公司可以在城市里消失一个星期。所以那里要有 wifi,要有打印机,要有办公场所,有饭吃。这个,资本家肯定会很欢迎的,算是给你疗养了,但你又在干活,晚上还可以搞搞团队建设,增加凝聚力。这个模式如果能被开发出来,就不一样了。
B:对于你们设计的需要村民参与的项目,他们的自主性如何?
L:目前中国的乡村,由于 100 年前士绅阶层破产之后进城,陆陆续续经过几次折腾,有机会的人都从村子里溜走了。原来乡土文化有生命力因为它多元,村子从无限多元,到现在非常单一,不健康了。
我们所说的 co-design,协同设计,与社区结合,你要先去定义谁是社区。我并不认为目前在物理上占据乡村的人,是唯一的或最合理的主体。我的合作对象既有村民,又有村子以外的人。以后乡村的社区,应该有新的人进来,才是好的循环。村民可能会想,为什么我们村子要别人进来?但其实长三角地区,移民是很多的,光“太平天国”,人口就损失大半,然后新的移民进来,现在又有三峡的移民。为什么长三角看不到安徽那样的老房子,没有宗族力量?原来我们一样有强大的宗族力量和漂亮的房子,因为“太平天国”以来,历次战争基本上把这里打平了。我们看未来,应该把界限打破。水土流失了,怎么让水土再回来?让知识分子回到乡村去,喊口号是没用的。但是反过来,如果有机会你去吗?如果有人成功了你会去吗?如果这件事很潮你去不去?以前资源都往城里跑,以后会往乡里跑,你反而觉得这是我的机会,这是我的生活。
B:关键是让大家觉得乡村是一个和城市相当的选择。
L:对,在农村你可以用土灶做饭,比较香,城市里用电饭煲更方便,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只要让大家有选择,可以流动,就是好的社会。我一直在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对应的,你不能说乡村搞得干干净净就不像乡村了。种粮食决定了它是乡村,在乡村不一定所有人都种粮食,但是会从事和粮食相关的行业。我们现在的逻辑是,种粮食只要 10%的人就够了,另外的人干吗?进城嘛!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实上和粮食相关的行业很多,需要很多专家的。经营农场的人不一定自己种田,喜欢就种,农民为你种田可以有三倍收益。我做这个项目不是反对城市化,我做的不是乡村设计,我做的是城乡交互,接下来我还要做都市农业。
B:是什么促使你关注乡村的?是不是也受到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先驱的影响?
L:在中国做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关注乡村的,我们的文化基本上就是乡土文化,像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我不可能不受他们影响。知识分子还是要有社会关怀的。
B:你现在做了这么多和乡村有关的事情,退休之后,你会想到乡村去吗?
L:没问题,而且这是很传统的道路。中国的传统社会很疯狂的,我们说它不好不好,但是它有很好的地方,有义学、义田,很社会主义的东西,穷人的孩子也会受到很好的教育,连饭都没得吃的范仲淹还能出将入相。过去很有意思,人们通过科举制度进城,然后还乡。这个循环很有意思。我相信走了这一圈,你再去劳作,会看到更多。不管是《论语》也好,《老子》也好,都讲躬耕的人都是有大智慧的人。老贾在讲他的生活哲学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有大智慧。当你看着生物生长、斗争,花很多时间思考它,你进入的深度是很深的,不像我们,旁征博引、看上去很科学的论文,其实没有走到那么深。
关于设计丰收:
设计丰收(Design Harvests)是基于“设计思维”的战略设计项目,旨在建设一个鼓励可持续社会创新的创意社群,针对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思考设计如何主动介入,为这个中国“大”问题提供设计策略。
2008年起,设计丰收与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芬兰阿尔托大学、瑞士伯尔尼大学、荷兰鹿特丹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和IDEO,OMA等业内顶尖企业合作,以崇明岛仙桥村为基地,探索设计主动介入和解决社会大问题的路径,我们通过设计和创意链接城乡资源和需求,通过小的、系统性的改变来激活城乡关系。如同针灸,在关键穴位的刺激来实现对整个肌体的调适。我们将她称为“一个针灸式的可持续设计方略”。设计丰收项目已于2011年进入实践阶段。
设计丰收基于对乡村生活方式的潜力进行发掘、改良、提升和普及,结合城乡需求,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城乡创意协作网络,主张通过设计支持农业,通过设计支持创业,吸引设计创意社群进入农村,年轻创业者到农村创业,推广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善乡村经济、环境、就业和服务。
设计丰收官网:http://www.designharvests.com/
娄永琪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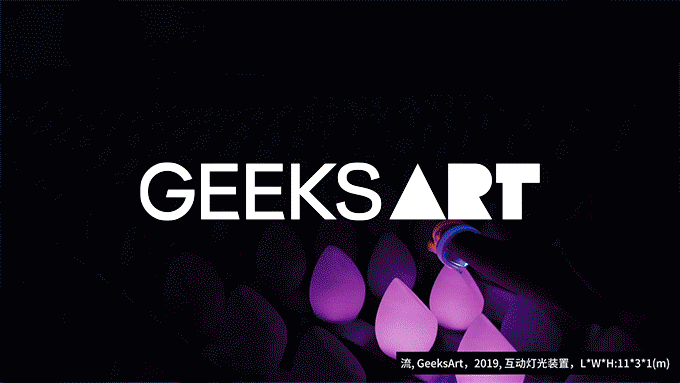








1 comments
Hi-设计 says:
5 月 7,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