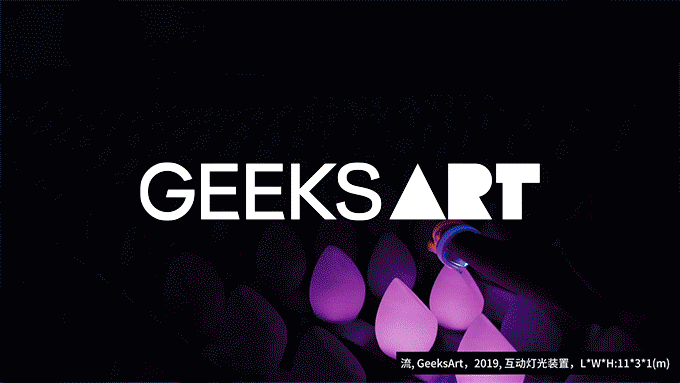早上9点半的早会结束后,蒋友柏双手背在身后,在方正通透的办公室里走了一圈,不时停在某位员工旁边指点沟通,那场面看起来,就像是在监督课堂作业。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他说只是在看看他们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够好。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细致地去观察员工的工作状况,“因为这关系到客户的利益,还是要看一下。这倒不是工作的紧张,因为这么多年,工作的这种状态都已变成了一种习惯。”

问他的下属会不会感到紧张,回答一律是:“没有啊”,“老板很好啊”……
采访那天,蒋友柏穿着一件深色条纹T 恤,包住一身已经练得非常到位的肌肉。蒋友柏每天去健身房3个小时,用短短3个月时间练出了一身别人需要1年才能练成的体型,并且坚信“胸肌连到肩膀才好看”。与媒体打惯了交道,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时,他不用人指导,也能摆出非常酷的姿势。
蒋友柏戴的眼镜是自己公司的设计,也是橙果设计最新的产品。在这个名叫“KDX 看东西”的眼镜产品中,蒋友柏第一次将眼镜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世界上还没有什么眼镜品牌用文化来定义。”他说。
对记者来说,蒋友柏并非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他特殊的逻辑思维和说话方式,让记者自信满满地抛出去的问题像撞到一块海绵上,落地无声。他讲话很快,而且是碎片式的、跳跃的,你必须半听半猜才能领会他的意思。那些生意人应该具有的圆滑、世故,所谓的说话技巧,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体现。正是这个习惯了以硬碰硬、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蒋友柏,带着橙果设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变成了最赚钱的设计公司之一。
咬牙度过艰难时期
每个公司都会用某种特别的形式庆祝自己的10周年,在橙果设计的第10个年头,自认为“从来没有好好地写过一本书”的蒋友柏写了第一本他自己真正想写的书—《第十九层地狱》。
虽然在这之前,他为大众所熟知的著述也有好几本,但都是迫于别人的面子发表的。《悬崖边的贵族》、《悬崖下的小道》、《蒋道设计》,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让蒋友柏为大众知晓的出版物,在他看来,都没有他所认可的阅读价值。
《第十九层地狱》是蒋友柏对创业10年的回顾与经验思考,以及个人对于创意设计的观察、理解与经营哲学。这10年的历练过程,毫无疑问是炼狱式的。除了事业方面,《第十九层地狱》还有蒋友柏对自己少年时代家道中落之后的那段日子的“忏悔式”陈述。
12岁之前,蒋友柏生活在天堂中—住大房子,吃饭穿衣都有佣人服侍,出行都是配有司机的轿车。但12岁祖父去世,家道中落,他一下子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不仅再没有之前富裕的生活,就连过去所有的价值观都轻易被推翻。但因为年轻,因为幼稚,他依旧和其他富家子混在一起,泡吧、泡妞、追求奢侈品,挥霍了大把光阴。“但当自己屈着身体躺在离天堂19层远的地狱时,我反而看到了天堂的全貌”。从美国留学回到台湾的蒋友柏,像突然开化了一样,变成了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他没有服从家族的期待和安排,没有从事银行、投资、律师等等首选行业,而是出于对任何与贵族相关的行业的鄙视,选择了设计。
然而,2003年时的设计在台湾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产业,“设计在政与商的眼里,就只是台面下的戏子,没有实质的正视理由,却有着弃之可惜的娱乐价值”。橙果的使命,就是了解并破除这种错误认识,这也是橙果崛起的第一步棋。然而,橙果的最初几年充满了艰辛,蒋家第四代的身份对他的事业并没有什么帮助,而他也因为缺少经验一度受挫。他第一次与设计大师 Michael Young 合作,是承接一家银行预算 600 万台币的赠品设计和生产案,本以为大师的设计客户一定满意,但结果图很美,却没有人能生产出来;勉强生产出来以后,大师对材料又不满意,制作出了一批不堪回首的失败品。
为了度过最初的艰难,这个在员工眼里“强硬不可一世的霸气”老板,“原来是咬牙和血吞过来的”。他跑到捷安特公司,跟管事的人说:“我真的很想做你们的案子,但我不懂设计,也不会画 3D 模拟图,但我真的很想做你们家的生意,你们给我一个案子做做看好不好?”于是捷安特给了他一个30万的单子。
公司唯一一次周转不灵发生在 2008 年的农历新年前,蒋友柏必须面对辛苦了一年却无法领到年终奖的 40 位员工。当时,他能凑到的只有 8 万新台币,所以把员工们聚在会议室里,一个一个地道歉,用内疚的态度,发出每人 2000 元的红包,希望心意可以弥补金钱的不足。但是,依旧有员工指责他,身为一个老板,哪怕是去贷款、负债都要筹到足够的钱来发年终奖金,要不然,就不配以老板的身份创业与领导。
如今的橙果设计已发展成为“橙果设计”和“白木顾问”两个公司并行发展,服务五六十个客户;从当初磕磕绊绊地成长,到今天进入不太担心钱的时期;从低三下四求客户,到现在有了“不对牌的客户,再大也不要”的牛气。但正因为有过以往的低谷,如今的蒋友柏一点也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时刻将自己置身于“第十九层地狱” 中。“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着相同的‘地狱进行式’。随着心智的成熟,背着越来越重的十字架过活会成为习惯。当不能享受时,就承受;到不能承受时,就忍受;而不能忍受时,就接受。一旦学会平和地接受人生十字架,就会找到在地狱进行式中享受的方法。”所以,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或者说难以置信的寡淡生活,对于蒋友柏而言,都是常态。
不知累为何物的蒋老板
作为蒋家的第四代,他说,“蒋”这个姓于他是一种原罪。橙果设计创办初期,蒋友柏和橙果设计更多的是出现在娱乐版而非财经版。蒋友柏记得,他曾经用两个星期时间认真准备一家财经杂志的访问提纲,并且在访问中不厌其烦地向记者介绍他的设计理念,但两周后刊登出来的杂志封面,却是他与其他名模的合成照,并被定义为“美力”的成功。
直到今天,橙果设计还是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一家自以为是的假设计公司,靠的是行销手法与知名度,而不是专业与执行力。
就连很多刚进公司的新员工,也常常会以为蒋友柏只是一个隔三差五跑来露个面、但其实不干半点实事的挂名老板,来了以后才发现,在早晨 7 点半给他们开门的不是熬夜未归的某同事,而是这位老板。蒋友柏给自己设计了一种堪称苦行僧的生活习惯,过去的 5 年,他每天 5 点半至 6 点间起床,起床后清理狗大便,叫小孩起床,7 点准时出门,8 点前出现在公司楼上的咖啡厅。
下午 2 点钟是蒋友柏的下班时间。3 点前,每一天自动进入第二阶段的生活时间。直到 9 点半小孩上床之前,他的时间都属于孩子和 9 条狗。晚上 10 点钟,他进入第二段工作时间。睡觉时间视工作情况而定,一般在 11 点至凌晨 2 点之间。
在员工眼里,蒋友柏是一台永动机。10 年来,他每年要写 300 份报告,相当于每天写一份。无论是晚上 11 点还是早晨 7 点,收到的工作邮件,他一定会在半小时内给予回复。每天开会、谈案子、聊创意、找员工谈话……永远就没有停歇的时候。一位在橙果工作5 年的下属说:“我在橙果 5 年以来,似乎未曾看到老板因为生病而请假,人总难免会有病痛的时候,但我的老板从来不轻易表现出不舒服,或说真的让我们看出来了,他也会轻描淡写地说他很好……”员工之间,关于老板“独裁”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个老板,发火的时候、想到好点子的时候,都会口无遮拦地爆出三字国骂。难怪一个女员工这样评价他:“他骨子里就是个绅士:满嘴脏话的绅士。”
蒋友柏承认,自己的个性实在不适合与人相处,“一个同时拥有那么多自负、自卑、自信、自惑和自利的贵族后代,绝对会让周遭的人感到无比无奈与无言的压力。”他的朋友数量,两只手数得完,可以相信的人,一只手还嫌多。那些与他一起经历了公司的种种生死起落依然留在身边的伙伴,都成了他交心的好友,成了公司的顶梁柱。“这些柱子,才是我在设计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最骄傲、最有自信的回礼。”
“台北最好玩的一点就是什么都没有”
Q:《第十九层地狱》是一本怎样的书?
A:这是一本很怪的书,不管是内容还是包装、设计。这也是第一次自己为了出书而写的书,以前的不是,以前是别人要我写的,或者是我的讲稿整理而成的。《第十九层地狱》的写作我从头到尾没有停过,事实上我要做的就是一本可以从头到尾不停顿地读完、一读到底的那种书,这本书是没有断页的。现在的出版已经很久没有改变了,我试图去改变出版的定义。我们还为这本书开发了一个 app,只针对苹果用户,没有针对 Android 系统,因为我觉得 Android 跟我的个性不符。
这本书比较好玩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我的个性定义出来,所以它并不是以卖为出发点,而是以我们能带来什么样的新意为出发点。所以这本书里面还会有歌,我自己写词,请刘轩做的一首歌,而且这个歌是你可以自己去重新mix 它、变成是你自己的一首歌。这里面也有图,有我所有的刺青,你也可以把它刺在你身上。你可以发现很多好玩的东西,所以我不把它定义为一本书。
虽然我写的方法只是很平静地叙述了一个我看到的事情,我并不是想要去说服任何人。很多出版社的意图是写书是为了赚钱,所以要写大家看的东西。但我用这个去赚钱,不是很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吗?另外,为什么我写的东西要大家喜欢,或者说符合大众的品位?这好像跟书的观点不一样。
出版业从来没有改变过形态,作家为了版税,流行什么就写什么,但以前作家不是这样。大陆现在把作家当什么?当作明星炒作。作家本来就不是明星,作家是文字工作者,所以这次我不打算做书的宣传。我想,这本书是颠覆了很多东西,有倒回到原点的感觉。
Q:你追求自由创作、不受市场干扰的个性,会否让你在做公司的时候受到很多挫折?
A:会。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基本上过去五六年,即便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也没有让客户赔过钱,这些就是你的经验值,有了这些,你才会有选择权。现在不是说客户来选择我,而是如果客户不对牌,管你有多大,我就是不要—因为我不缺钱。说真的,没有案子我也可以活得很好,公司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资本,都是这些年用吃苦拼出来的。所以你自己有选择权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更多地做自己,而且做得更精。
Q:选择客户有洁癖,那生活中你会不会也有消费洁癖?
A:付得起就买,付不起就不买,这就是我的消费观。所有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新鲜不新鲜,只有记忆深不深刻。记忆深刻的东西,我刚好也需要,为什么不买?就算贵,我认同啊,就会买。我在台北很少买东西,出境倒会经常消费,觉得已经全家出境了,就要带一个记忆回来。
我对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买东西是看到喜欢的、觉得真的是需要才会买。我负责这么多客户,随便看一个东西,就会知道它的成本多少,怎么卖。没有办法,做了那么多年,很自然就会把它解构开来。
Q:你觉得现代设计总体来说,是过多还是不足?
A:我觉得不是过多或不足的问题。以哲学来讲,产品最大的功能就是做到中和,是一个物体和周遭的关系。你只要抓到这个,产品不会过多或者过少。你觉得过多是因为很多产品都很突兀,不知道要不要有;你觉得过少,是因为你觉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好像就那几样。设计的美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对我来说,设计的重点不在于美感,而在于策略和商业。
Q:你不在台北消费,但台北对你来说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
A:没有。我都快疯了,台北最好玩的一点就是什么都没有。
Q:那你所欣赏的城市是哪里?
A:我其实还好,去哪里都是一样,是新鲜的感觉。夏威夷我们常去,很喜欢那里的感觉,日本也常去,喜欢他们的态度。新加坡还好,四年去一次就好了。迈阿密也不错。小孩子澳洲还没去过,想去看看动物。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目标,基本上是哪里适合小孩子和家人去放松的,我就去哪里。我去的任何城市,都能找到一些新的不错的东西。对我来说,好玩的地方一定是要适合家人。
Q:你是家庭感很重的人,是如何做到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的?
A:我分得蛮开的。当然,脑袋基本上一直会在想工作的事情,但只要我离开办公室,还是尽量回到生活中来,这是经过很多年的锻炼才能做到的。我真的不喜欢把生活和工作混淆。我的客户就知道,只要我离开办公室,电话打过来我一定是不接的。等小孩子睡了,我才开始一个一个回电话。